法律英语那些事儿之“谋求”
 2018-05-08
2018-05-08
 1469次浏览
分享到:
1469次浏览
分享到:
前几日,我们的香港客户邮件咨询其境内附属公司所签署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中某句话的法律约束力。那句话是这么说的:“承让方承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日后之三年内谋求目标公司偿还包括出让方的现有股东之欠款。”不出乎意料,“谋求”二字显得很扎眼,不禁让人想起了英语里的“best efforts”。
对于“best efforts”,不少律师目光都落在“best”上,认为沾上该词就应具有排除万难、穷尽一切手段(extraordinary measures)以达目的之含义,哪怕是有损承诺人自身利益也应在所不惜呢。你瞧,这是不是与小情侣们海枯石烂的山盟海誓颇有无异曲同工之妙?
Kenneth A. Adams在其A Manual of Style for Contract Drafting引述几个美国法院的案例,我们现摘录如下:
Coady Corp. v. Toyota Motor Distributors, Inc., 361 F.3d 50, 59 (1st Cir. 2004),法官认为, “ ‘Best efforts’... cannot mean everything possible under the sun....”;
Triple-A Baseball Club Associates v. Northeastern Baseball, Inc., 832 F.2d 214, 228 (1st Cir. 1987),法官认为, “We have found no cases, and none have been cited, holding that ‘best efforts’ means every conceivable effort”;
Bloor v. Falstaff Brewing Corp., 601 F.2d 609, 614 (2d Cir. 1979),法官认为, “The requirement that a party use its best efforts necessarily does not prevent the party from giving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to its own interests.”
既然“best efforts”不是那么地义无反顾和不计后果,那么,什么是 “best efforts”的衡量标准呢?有法院认为“best efforts”的衡量标准是 “good faith”, 有的法院认为应高于 “good faith”,也有法院认为是 “diligence”,还有法院认为是 “reasonableness”。案例就不再一一枚举了。总之,一个uncertain的词不可能有certain的含义。
虽然法院对“best efforts”的衡量标准尺度有所不同,但绝大部分法院认为“best efforts”之承诺有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可以执行的(enforcea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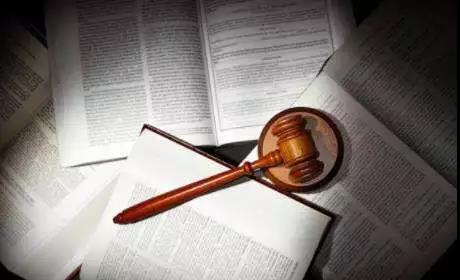
在国内法院判决中,因本人技术和知识所限,未能检索到关于法院对“谋求”和“尽最大努力”字眼的论述。但我们检索到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比如中国农业银行玉门市支行与玉门康庄农林牧科技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12号]。
在该案中,当事人(农行玉门支行)向债权人(玉门信用社)书面承诺“保证负责收回贷款”。法院认为,不宜按照担保法上的保证认定责任。理由为:(1)担保法意义的保证是保证人提供保证时,以自身财产偿还欠债作为保证内容的,而本案的“保证负责收回”是履行一种行为,二者有所不同。(2)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农行玉门支行承担的是保证责任,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要求农行玉门支行承担保证责任缺乏合同依据。因此,农行玉门支行违反了承诺义务,属于不作为的违约行为,由此给玉门信用社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当然,类似的案例还有关于“协调解决”和“督促偿还”的,判决结果基本相同:即不宜按照担保法上的保证认定责任。在此不一一枚举。
转了一圈回到我们的邮件答复。针对客户关心的可否让承让方来替目标公司偿还贷款,我们的答复是:我们理解,“承让方承诺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日后之三年内谋求目标公司偿还包括出让方的现有股东之欠款”尚不等同于承让方代为清偿的意思表示。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否则该等规定并不能产生必须由承让方偿还出让方股东之欠款的法律约束力...[此处省略几十字]
建议结合我们的往期文章《法律英语那些事儿之合同“促使”》以加深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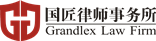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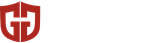

 返回列表
返回列表





